


2016高考零分作文:我已经无话可说了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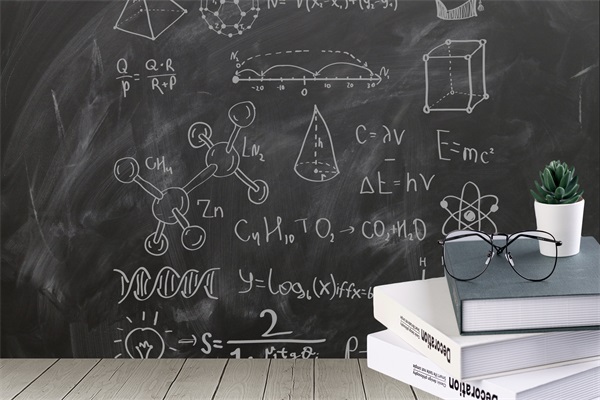
在我残存不多的记忆片段里,能苟延残喘般回忆起有关于这个世界的。
那年,世界还处在混混沌沌的灰暗之中,人民大众在水深火热中饱受煎熬,苦苦支撑。我睁开眼睛,观望这令人叹息的世界。窗外吹着寒风,飘着雨丝,我“呜呜”了两声,便不再反抗,兀自睡去。那是20世纪的比较后一个年代。
三岁那年,我叉开双腿弯下腰从自己的胯下俯视那东南方向的半片天空,一排大雁呈人字形飞过。随着来自西北方向“呯”的一声枪响,一团黑乎乎的东西从天空直坠下来,恰巧堕入我的两腿之间。经我鉴定,那是只美丽的雌性大雁。此后,我断言,这玩意不简单。那年,我自诩为“虚无”,暗指这缥缈的人生。
1999年12月31日,23点59分,我坐在马桶上,开始意识到老师让我带回家让家长签名的34分的数学卷子,我还折了四折夹在语文课本的77页。忧心明日老师喊我去办公室背九九乘法表,我却只能流利的背诵一一得一至一九得九,之后就得卡壳。又回想起,语文老师在我周记本子上批阅后留下的三个红红的大字,“流水账”成了多少人的笑柄。这年,我像困在笼中的黄雀,得不到自由然后变的忧郁。
03年,也就是六年级的下学期,我开始适应这个小学所谓的微元社会。开始肆意在校园里横行,驱赶幼年级的乒乓球桌。开始笑话一二年级的**手拽着五毛钱,挤到小卖部,眼神坚毅,语气坚定得大喊,来两包唐僧肉。开始情窦初开,抢漂亮女孩手中的牛奶饼干巧克力借以引起她的关注。也是这年,毕业考后,几个同学聚在教室大刀阔斧谈论未来,夸夸其词十年后事业有成再来相会。
同年9月份,我首要次听说了中考,高考。至此时间好像变得极其抽像了,像光滑的火箭冲天直上,沉重的力量压抑着我。我徘徊在学校和家之间,在教师家长面前极力表现得乖巧,在周末有闲也总约人上山涉水干点勾当。我像裹着庄正外衣的黄鼠狼,有人说我太深,看不懂,大抵也是如此。
中考后,我有幸有了一批牌友,高考后,我有幸有了一批酒友。如此禁锢思想的教育体制,我想我已经没话可说了。
-
报考二建需要社保吗
学大教育
-
学历提升教育机构排的状
学大教育
-
在职人员有必要学历提升
学大教育
-
提历报考什么专业比较好
学大教育
-
 吉林法学专升本分数线(2016-2021)
吉林法学专升本分数线(2016-2021) 2021-08-11
2021-08-11
-
 吉林护理学专升本分数线(2016-2021)
吉林护理学专升本分数线(2016-2021) 2021-08-11
2021-08-11
-
 吉林工商管理专升本分数线(2016-2021)
吉林工商管理专升本分数线(2016-2021) 2021-08-11
2021-08-11
-
 吉林汉语言文学专升本分数线(2016-2021)
吉林汉语言文学专升本分数线(2016-2021) 2021-08-11
2021-08-11
-
 吉林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升本分数线(2016-2021)
吉林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升本分数线(2016-2021) 2021-08-11
2021-08-11
-
 吉林电子商务专升本分数线(2016-2021)
吉林电子商务专升本分数线(2016-2021) 2021-08-11
2021-08-11
-
 吉林财务管理专升本分数线(2016-2021)
吉林财务管理专升本分数线(2016-2021) 2021-08-11
2021-08-11
-
 吉林工程管理专升本分数线(2016-2021)
吉林工程管理专升本分数线(2016-2021) 2021-08-11
2021-08-11
-
 2016开学课观后感400字
2016开学课观后感400字 2020-12-24
2020-12-24
-
 2016浙江高考零分作文:高的心声
2016浙江高考零分作文:高的心声 2020-11-06
2020-11-06



